在金宇澄看来 细节是细微的时代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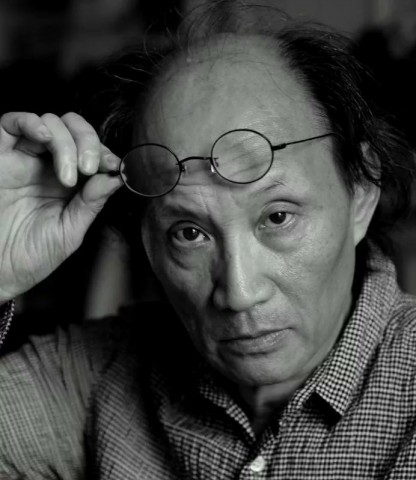
摄影/王寅
“长锦号”划开灰色的浊浪,由上海驶向北方。低沉的云头几乎垂落海面,寒风刺骨,甲板上星星点点的军绿色,在此刻阴霾的天空下略显黯淡。这群十六七岁的年轻人,身着上海市政府发放的棉衣四件套,从上海出发,在大连上岸,四散至长春、齐齐哈尔、牡丹江方向,然后去向各处的田野??
1969年,东北、内蒙古、贵州、云南、安徽、江西等各省代表在上海锦江饭店开上山下乡动员大会,每个中学老师去听,然后回校动员,必须做选择,“场面等于招商会。”金宇澄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笑着回忆。
前往黑龙江务农,“棒打狍子瓢舀鱼,野鸡飞到饭锅里”是该省代表描绘的风景,因为“家庭成分不好”不能选军垦单位,金宇澄最后去了黑河地区嫩江的农场。一起出发的上海青年们,来自卢湾、静安、闸北、普陀等“上只角”“下只角”,离开他们熟悉的新旧里弄、石库门和工人新村,这些中学生,小学辍学者,无业闲散青少年野??泥沙俱下,带着樟木箱,老式皮箱、绣花丝棉被、父母塞到行囊里的上海吃食、地下交流的翻译小说,伙同他们的青春,投放到几千里外陌生油黑的土地。
从16岁到24岁,金宇澄在嫩江度过了自己黄金时代的八年。他的新书《碗》,以及中短篇集《方岛》,即取材于这一代人的体验。
“不响”
数千名上海小青年,从大连港下船,转乘火车、解放牌卡车一路向北分散,金宇澄来到了此次的终点站嫩江。这里是国内最大农场, 苏联专家设计,拥有13个各占地1500公顷的分场,俄式红砖大礼堂,可容纳五百人的食堂,宿舍是睡四五十人的大通铺。
金宇澄回忆这些,仿佛一切就在眼前。
“到达后第二天就开大会,上海几百号男女,哈尔滨、天津小青年,坐入大礼堂,领导在台上说:‘家里有问题的站起来’。有五六十人起立吧。”金宇澄回忆。在互不认识的情况下,陆续有青年人开口表态,决心与“有问题”的父母划清界限云云,表明心迹,主动站队的声音在礼堂激荡。金宇澄“不响”。
当时表态应该是成熟生活的标志,“对于接下来的工作安排,相对就好些,在仓库当保管,或管理食堂,面粉厂做班长。我是务农,闲时打杂,盖房子、装窑、砌火炕,做豆腐、粉条。”金宇澄说。
他几乎进入了当地所有的人家,修火炕、修炉子。“走进老乡家,有时根本无法呼吸,每户都养猪,饭锅和猪食锅在一个锅台。我记得有一家的女人,做油饼非常有名,她生了小孩,那孩子当时拉了一泡屎,我就在旁边,女人随手撸起炕席上的稀屎,一把就甩在地上。我无法呼吸就跑出房外。我的同伙追出来说,跑什么啊?过会儿人家就给我们做油饼。”
金宇澄的童年在上海“上只角”度过,那是外祖父买在陕西南路的洋房,很长一段时间,他熟悉街上的白俄面包房、牛奶房、钢琴店,附近的教堂、花店、影剧院,都让他以为整个上海都是如此。
他尽管努力,也难以真正融入乡下的环境。部分上海小青年在黄昏议论上海的生活细节,他排遣寂寞是靠读书写信,相互交换从上海带来的小说,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罗曼·罗兰、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《悲惨世界》。
农忙时参加割麦,留守农场的“刑满释放”者“手把手”教这些小青年如何握锄,辨别豆秧和杂草、如何磨刀,如何割倒麦子、捆扎、码垛。
金宇澄把这些过程写在信里,朋友建议他可以写小说。而直到近二十年,他才动笔,取材当年,以中短篇的形式发表,很多篇章超出一般生活的经验,奇异,如天方夜谭。
蛰伏
1977年高考恢复,不少青年志在一搏。他身边一些“情绪低落”者却没有报名,他们仍然不相信好事会落在自己头上。最终他以“病退”回沪,成了里弄钟表厂的一名工人。
“我师傅姓秦,钟表厂八级钳工,额角戴一只钟表放大镜,讲宁波口音上海话。1980年代初,上海尚有无数钟表工厂,我随秦师傅踏进车间,眼前一排一排上海女工,日光灯下做零件。” 金宇澄曾在《史密斯船钟》里这样写道。
进厂几年,计划经济节节败退,钟表业走下坡路。本不担心销路的产品被香港电子表和不再紧俏的瑞士表取代,研制热门的洗衣机定时器,工艺并不复杂,但需要不同的技术设备与材料,单靠八级钳工的双手做的模子,精度远远不如日本产品。没有洗衣机厂要这样的货。
如今回想,金宇澄感慨:“这里有多少内容,都被城市淹没和吸收了。上海是大海,容量非常大,看起来平静无波。”
这些机器、师傅们以后陆续消失了。工厂拆了,改做房地产,其间他因为写作,进入区文化宫。
一年上海下雪,让他想起北方的鹅毛大雪。那时他一个人躺在北方发电厂的露天冷却池里,被温暖的池水包裹。第一篇稿子就写北方的雪,一投即中。
他写了六七篇北方记忆题材的短篇,《失去的河流》《方岛》获1986、1987年《萌芽》小说奖,《风中鸟》获得1988年《上海文学》小说奖。金宇澄调入作协,成为《上海文学》小说编辑,每周上几天班。
初来乍到,老主编周介人要他编一篇老作者的短篇,那是手写稿的年代,他用红笔,最后把稿子改成大花脸。“那稿子确实差,周老师非常吃惊,说没见过敢这么改的人。”他回忆。
这期间他仍然写小说,《轻寒》发表在1991年的《收获》上,随后逐渐进入写作的瓶颈——职业编辑的挑剔习性,是双刃剑,对人对己都如此,白天当编辑,晚上写作,往往第二天再看自己写的句子,感觉不顺眼,改来改去,最后也就搁笔了。这是一种选择,要么写作,要么编辑,金宇澄选择后者,做了近三十年。
摄影/王寅
“新腔”
2011年5月,金宇澄偶然进入“弄堂网”论坛,这是上海网友的平台,世界各地的上海人在此聚集,七嘴八舌聊老上海“事体”。浏览中不免手痒,于是,金宇澄化名“独上阁楼”,用上海话开帖,每天更新这部《繁花》初稿——当天即引动网友关注,不时有人跟帖搭讪:爷叔是谁的马甲吧?爷叔,后来呢?后来什么情况?受网友鼓励,金宇澄欲罢不能,写到陶陶出场卖大闸蟹,意识到这么写下去,是长篇小说了。暂停两天,做了一个结构大纲。此后是以每日打卡般的自律,近七个月完成全文。
“《繁花》是通过一个自由自在的过程写出来的”,可以隐匿自己,等于换了一个人,到一个陌生地方,面对一群陌生人,脱掉一身束缚,尝到一种自由的状态,无所顾忌,回归母语,可以做各种实验,可以用鸳鸯蝴蝶派的旧词,可以随时修改人物名字,最重要的是,可以随时触摸到读者。
金宇澄比方这种状态,等于“一个小孩子当街翻跟头,周围越有人叫好,孩子就翻得越来劲,这是一种写作激励,天天写,天天得到认同与疑问。” 这形式吸引他进入,吸引他放下长期职业编辑的状态,最大化输出自身的所有能量。读者的即时反馈,让他投入更多的热情与警觉,让他知道阅读的各种角度,发现读者中卧虎藏龙。“长篇写作,一般是孤独面壁数载,成稿后也是一对一的孤独关系,编辑给一个千字意见,已算认真。而网上始终是众声喧哗,天天有各种观感,所以,我这样的写作,极为奢侈。”金宇澄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网友日日催促,作者热情也日益高涨,不吐不快、甚至到寝食难安的程度,必须每天保持更新。一次他去外地出差,电脑故障,天蒙蒙亮只能找到一个网吧去写,这是他每天的写作时间。
金宇澄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感慨:“我原来一直特佩服民国时代的连载作者,天天写了就发,其实习惯以后,是不难的,因为你已经时时刻刻在考虑想表达的内容,这也是我们已经遗忘的文学传统,狄更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是每天写一节就发。鲁迅《阿Q正传》也是这样的连载,这方式让你更有写作热情,也更警惕,对读者更了解,等于你如果每天要直播,内心就更冷静,考虑也更多,更有想法。如果决定这样做的话,你经常就是超常发挥,无所畏惧。”
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和金宇澄是老同事,三十年来在一个大院里上班。得知长期搁笔的老金,不声不响写出这么一个大部头,决定配发两篇评论,予以同期刊发,这在《收获》历史上是首次。发表以后,程永新第一时间就收到不少作家微信,找他聊《繁花》。再以后,《繁花》成了口口相传的热门书,甚至娱乐圈小鲜肉在“丢书大作战”中丢《繁花》,立刻被赞有文化。
也因此,金宇澄被人们认为是小说界的“潜伏者”,他的总结,是长期的编辑经验,修正了他的写作路径,“小说家看得最多的是名著,编辑看最多的是稿件。因此我更多了解当下的写作状态,什么样式可以不写了,什么可以写,哪一种形式和内容是少见的,如何显示个性。”
“《繁花》并不是提倡沪语写作,假如大家都已经这样写,肯定没这本小说。”金宇澄说。他认为《繁花》的特色,是脱离了普通话北方语系的写作,从头到尾用苏州口音的上海话,因为金宇澄父亲是苏州人,这种上海话更雅致些,“昆曲就是苏昆,是苏州话的说唱,言词文雅,特别通文”。
此外就是少见的“话本”样式,完全区别于常规的西化小说面貌,“这我知道没人去做,从头到尾让一个人说了张三慢慢拉出李四,让一个人复述很多杂七杂八人说的话,话中有话,绵绵不断,是我一直喜欢的中国味道,完全和西式小说不一样。扬州评话名家王少棠先生,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。”因此整部《繁花》的状态就是:一个评话先生在说,永远不停地说。
上海主持人曹可凡说,《繁花》不好朗读,用普通话朗诵怪怪的,纯用上海话读也拗口。金宇澄觉得这就对了,这是一本“可以在心里发声”的书。
《繁花》用改良沪语,是他精心修订的策略,将过于地方化的字词如“侬”完全删去,使得《繁花》没有第二人称,读者却很难发觉,保留上海韵味和短句式,保持一种阅读普适性,目标是让北方语系的读者能看懂。
金宇澄说,上世纪90年代以来,文学受了改编电视剧、电影的影响,“作者通常会更重视故事的完整性,而不是文本、语言的特征个性。”对于影视的改编,后者会完全被抹去,“但是小说最重要的,始终是语言,不是内容,你拿起一本小说,首先看的就是语言的状态,语言有没有个性是第一时间的感受,而故事要等读完才了解。”他提到周作人译的《枕草子》特别有个性,而林文月的同题翻译“很吓人”,这都是语言的作用。
“或许还是跟我当编辑有关,编辑这一行的,做梦都是在想哪一天可以忽然收到一篇语言特好的稿子,读三句就着迷。” 金宇澄说。
跨界
从一定意义上说,金宇澄更注重形式,不仅体现在文本和语言,也体现在生活方方面面,在朋友眼中,他懂生活,懂审美。
朋友毛尖说,“很久以前跟金爷吃饭,第一印象这就是上海老克腊。”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跟金爷在纽约购物,凡自己提溜回来的东西,到家就嫌弃了。跟着金爷一起买的,回来后人人夸。
如今,金宇澄画的插图,也成了招牌,笔触细腻,富有言外之意,跟金氏小说一样,打上了浓厚的个性标签。
他画的范围,还原熟识的生活,上海、东北;弄堂房子、麦田、连绵如波的屋脊,他画了上海最大旧货商场、国泰电影院;各种手工示意图、城市版图、街景变迁图野??他笔下的画,常常有奇情。高楼之上,伸出一只翻云覆雨手;静安寺安静地蹲在一个簸箕里;麦田里低头的向日葵,使他联想到低垂的照明灯颈,干脆给画中的每个人,都安上一顶向日葵灯帽。金宇澄觉得,“一幅画,可以让人看到时动一下脑筋。”
和《繁花》的缘起相似,金宇澄的画是玩出来的,是不经意间超常发挥。开初只是在打印过的A4纸背面,用普通圆珠笔涂鸦。《收获》副主编钟红明看了他为《繁花》绘制的街道示意图,建议他出书时自画插图。就此他画了《繁花》20图,《洗牌年代》27图,一发不可收。此次为新出的《轻寒》《碗》《方岛》,画了书封和自画像以及近30幅插图。
金宇澄说,他以前读到的东西方小说,都有插图,“文学和插图是紧密相连的,而如今很少有这出版意识了。但我仍然认为,这是有意思的事。另外是读者买你的书,作为作者,应该尽其所能。”每次出版,他会为每幅插图编号,附注,来回修改多次,细致讲究,一如他修订《繁花》不厌其烦,已然是一种本能。在他的微信朋友圈,可看见手绘封面的各种设计稿,交出版社的蝇头小字逐条标注对封面构图、色调,字体颜色、大小、位置、文案种种细节。
“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。”金宇澄说,也许,是上世纪70年代末,他曾经陪老父亲到上海龙华机场老机库,去认领家中曾经被抄的书的经历。巨大的仓库内,几乎是书籍坟墓,满目狼藉,满地碎纸,来人都找不到自己的书。父亲心痛之际,见一个小青年将整函线装书随便拆散,边走边扔,不由出言阻止。或许几十万破书的“流离失所”给金宇澄留下深刻印象,他觉得,书,应该有它最完美的颜值。
“八卦”
金宇澄并不认同“宏大叙事”。他曾说“细节是细微的时代史”。无论小说、散文都从细微的日常入手。金宇澄觉得“作家的位置在改变,托尔斯泰时代过于闭塞,读者都在茫茫黑夜中,无比需要听一个巨人说话。而今是信息爆炸时代,碎片化阅读时代,作者还站在高高神坛上是可笑的,也因为读者的卧虎藏龙,读者比作者更懂文学。”
“智者是非常少的,上帝是非常少的。上帝已死,个人的范围都那么窄,谁能看清亚马逊森林里到底有多少动物?我特别不信全知视角、高高在上的姿态,个人能理解什么,写你熟悉的内容就够了。我除此以外什么都不知道,我不知道人物心理,我活到60岁了,连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没搞清楚,包括我怎么来批判,我们一般意义的批判还少吗?”
金宇澄愿意放弃“内心层面的幽冥”,保持“不响”,让人物自己七嘴八舌,各有各的主张,他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世界。
“文学就是记录生活细部,记录人物的关系。看《金瓶梅》是看当时的人怎么相处,怎么吃饭睡觉,怎么吵架骂人。如果没有这本书,我们不知道明代的生活现场,文学起的是这个作用。”国人爱在饭局上说话,多少脍炙人口的立场和图画,诞生于流水席,然后消散于无声。他常常设想,如果有人用录音,选一百个饭店,每晚开录三个小时,请小说家整理出来,就是巨著。
或许在某种意义上,金宇澄就是录音的人,他发现饭局上每人的言谈,都进入一种创作状态,才能讲出有意思的内容。“从古到今,人都这么生活,这么爱听爱讲,这才是人性的特点。包括八卦。如果没有八卦,社会将是铁板一块,八卦是润滑剂。中国传统最漂亮的小说、笔记体都是八卦。” 他感兴趣的是“不太有人注意的人群”,《繁花》避开知识分子,其实是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小市民,“《围城》写了小市民生活,还是知识分子?” 他反问。
行文不断纳入纵横的比较,冷静剖析几代人的状态,表现人与人永远的不同,记忆与经验,时代带有的杂质,沉淀之后,花开花落,是金宇澄写作的方式。